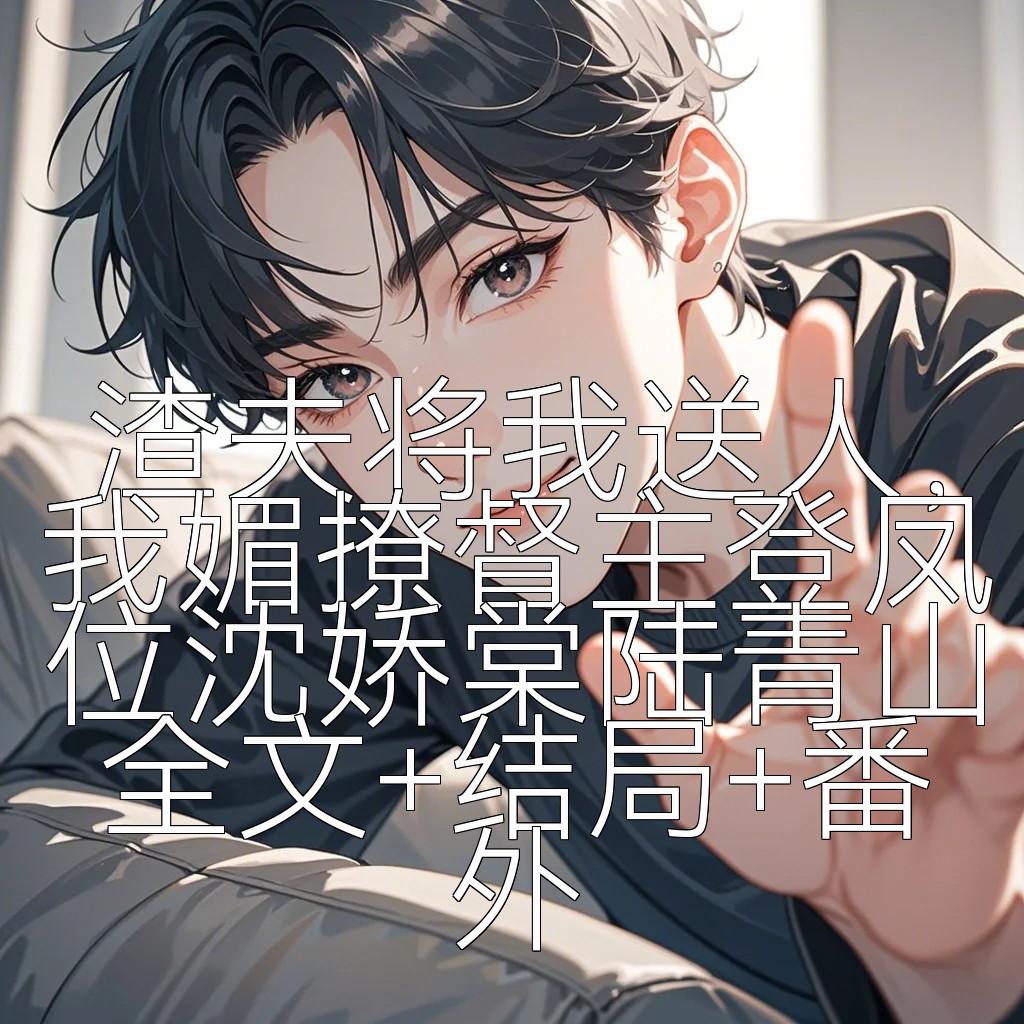- 蝉鸣落满旧时光全新
- 分类:现代言情
- 作者:落花若尘
- 更新:2025-07-17 07:56:43
- 最新章节: 第43章
《第43章》精彩片段
风托着种子寻方向,画笔接住晨光,镜头藏起温柔,蒲公英飞落时,心事已在他眼里扎了根。
湿地公园的木栈道旁,我看着白小薇把画具箱往草坡上搬。四月的风裹着湿意,吹得她发梢贴在脸颊上,画夹里露出半截画稿,是株沾着晨露的蒲公英,绒毛被她用留白液画出细碎的光,像随时会被风吹走。
“你再往前挪点,就挡住我拍蒲公英根系了。”我朝她喊,手里捏着刚帮她采的三叶草标本——这是她画植物时的“幸运符”。我们认识快五年了,从她在植物园迷路时把冬青当成香樟,到现在能准确画出三十种植物的叶脉纹路,我始终是她最忠实的“纠错员”。她总说植物是沉默的朋友,其实她自己才是——喜怒哀乐都藏在画笔下,要凑近了才能看清那些藏在叶脉里的心事。
那天下午的阳光穿过水杉林,在草地上织出斑驳的网。小薇正趴在画板上细化蒲公英的绒毛,忽然“呀”了一声,手里的水彩笔滚到了栈道下的草丛里。她伸手去够,指尖刚碰到笔杆,一道深蓝色的身影先一步弯腰,指尖稳稳捏住了笔杆。
“这里草下有碎石,小心划伤。”
男声带着草木的清润,像刚被雨水洗过的石阶。我抬头时,正看见小薇猛地缩回手,耳尖泛起和她画里虞美人一样的粉。男人穿着志愿者马甲,背后印着“湿地生态修复”的字样,裤脚沾着泥浆,手里还捏着个放大镜,镜片上沾着点草叶的汁液,显然是刚从植被调查现场过来的。他胸前的工作牌晃了晃,照片上的人眉眼干净,名字栏写着“吴磊”。
“谢谢。”小薇的声音比平时轻,指尖在画板边缘无意识地蹭着,把刚调好的鹅黄色颜料蹭出了个小色块。
吴磊把笔递回来,目光落在她的画稿上,忽然笑了:“你把蒲公英的冠毛画得有光,很像它们飞起来的样子。”他指着画中花茎的弧度,“这里的线条再软一点,会更像被风吹动的感觉。”
小薇惊讶地抬头,眼里闪过一丝惊喜。她画蒲公英三年了,总有人夸她画得像,却没人注意到她刻意在绒毛里藏的光影——那是她觉得蒲公英最温柔的时刻。男人背着的志愿者背包拉链没拉严,露出里面的笔记本,扉页上贴着片压干的蒲公英标本,旁边用铅笔标注着“2022.4.15 发现于芦苇荡边缘,根系深达30cm”,字迹和他的人一样,干净又扎实。
“你也喜欢蒲公英?”小薇的声音亮了起来,像被风吹响的风铃。
“算是吧。”吴磊翻开笔记本,指着其中一页,“我负责这片湿地的植被修复。蒲公英不只是好看,它的根系能固沙,种子落地就能生根,特别适合修复裸露的土地。”他指着远处的芦苇荡,“那边去年还是荒地,撒了批蒲公英种子,现在已经能看到成片的绿了。”
风忽然变大,吹得小薇的画稿哗啦啦响。吴磊伸手帮她按住画夹,掌心的温度透过纸张传过来,小薇握着画笔的手顿了顿,颜料在纸上晕开一小片浅黄,像极了蒲公英花盘的颜色。那天他们蹲在草坡上聊了很久,从植物的生长周期聊到水彩的晕染技巧,从根系的分布规律聊到画笔的运笔力度。我看着吴磊捡起小薇掉落的橡皮,看着小薇帮他拂去马甲上的草屑,忽然觉得湿地的风都变得柔软起来,带着种子破土的温柔。